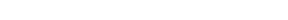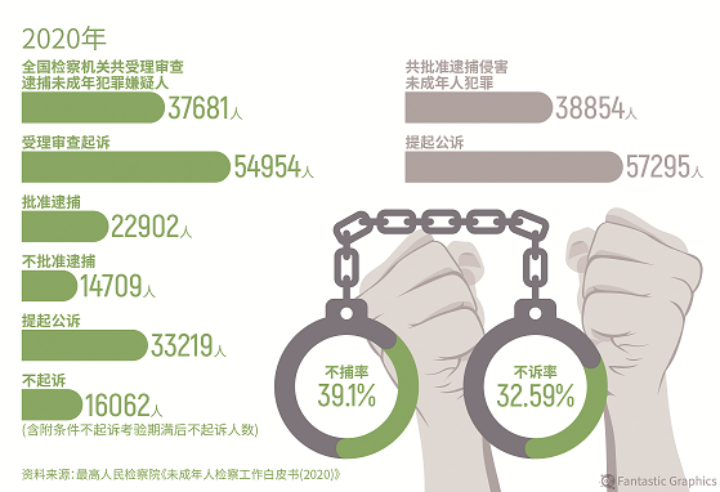
视觉中国
就犯罪未成年人而言,他们心智尚不成熟、可塑性强,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一部分犯罪未成年人还需要继续接受教育,如果给其贴上罪犯的标签,将不利于他们的教育改造,不利于犯罪的特殊预防,不利于他们未来的发展,阻碍他们正常回归社会。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就是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必要制度设计:封存对象为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主体为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行为人;封存条件为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这项制度在操作中与实际情况存在诸多冲突。
首先,与准入特定行业的冲突。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目的在于保障犯罪未成年人能够尽快回归社会,拥有正常工作和学习的权利,未成年人无需向任何个人及单位报告其犯罪记录。
然而,法律允许有关单位在得到司法机关允许的情况下对未成年的犯罪记录进行查询,我国民法与行政法甚至将一部分职业的准入门槛排除了有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这在我国法官法、人民警察法、检察官法中均有明确规定。
同样,律师法和教师法中也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但是过失犯罪的除外”,从而排除了曾受刑事处罚的人进入上述行业的资格。这些出于职业素养考虑的限制会影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行效果,不利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严格保密。
其次,与社区矫正制度存在冲突。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这4类犯罪行为较轻的犯罪人实行非监禁性矫正刑罚。此项规定让犯罪人在与社会生活不脱节的情况下,更好地回归社会,实现再社会化。然而,对于能够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来说,社区矫正更容易使得他人知晓。
再次,与公安机关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存在冲突。尽管我国刑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免除了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未成年人报告自己犯罪记录的义务,但实践中存在一些特定行业在招聘上岗时要求行为人到公安机关开具无犯罪证明。如果确实存在被封存的犯罪记录,那么公安机关当然不能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从而影响保密效果。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封存主体除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以及有关单位依法查询外,不得向任何个人或单位提供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义务,查询主体在查询后也具有保密义务。但对封存主体和查询主体违法披露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缺乏相关的追责和救济措施,必然会影响犯罪记录封存的实际效果。
因此,笔者建议进一步完善、细化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相关规定。为了更好地保护涉案未成年人,需要建立一套覆盖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对所有诉讼参与机关的统一法律规定,对刑事诉讼阶段形成的纸质及电子卷宗进行封存。
应进一步明确封存主体,确定刑事诉讼各阶段形成犯罪记录的司法机关为封存主体,负责本单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工作,具体承办人为直接责任人。并对封存的形式要件加以明确,例如,应当对犯罪记录封存的未成年罪犯卷宗档案标明“档案封存”字样,并进行单独存放,由专人实行保密管理。
应加强各部门协作,建立配套的衔接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一项系统工作,并不单纯是司法机关达成一致就能落到实处。应与户籍、人事档案、政审制度衔接,与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衔接,与社会帮教制度衔接。
同时,还应明确泄露封存记录的法律责任。当未成年犯罪人的犯罪记录被泄露时,法律如果没有赋予犯罪未成年人维护其权益的合法途径,那么这将导致封存制度形同虚设。
笔者认为,救济机制可以从两方面来构建。
一方面是公权力提供的救济。我国目前法律对于司法机关以及媒体等单位不当泄露或者传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责任未进行明确规定。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同时有着提起公益诉讼的职责,所以检察机关对于封存制度的有效实施负有监督职责。对于侵害犯罪未成年人利益的行为,可以直接发出书面的检察建议要求纠正,必要时也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另一方面,被封存的犯罪记录关系到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的评价。由于这些犯罪记录可以归入隐私权的范围,而公民隐私权受法律保护,所以当犯罪记录被不当泄露或者传播,致使未成年人权益受到损害时,未成年人有权提起侵权之诉,要求消除因犯罪信息泄露造成的不利影响,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韩山青 张文贞 袁媛)